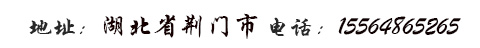月光与紫竹梅
|
上山的路,护坡被紫竹梅占满了。夕阳正好,海风也正好,这片深沉得有些老气的紫,忽然间泛起活力——我分明见它抖了一下,色彩也亮了几分,好像不再甘心贴在墙壁上保持静默,而是要挣扎着起身,想对我说些什么。可惜,我听不到,也听不懂。我只能看着那些粉色的小花从紫色的苞片中探出脑袋,在捕获到霞光后充满得意,如一张张笑意盈盈的小脸,然后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暗夜无人问津;那片紫随之失落,仿佛是被曾经的爱人遗忘,迅速黯淡。海风也在此停下,失了从沙滩一直冲上山的逸兴。人类用华灯拒绝自然界吐纳的节奏,我也深陷这场“征服”的游戏不能自拔。只有很少的时候才会想起,偷走月色的不是岁月,是自己。经常的,在夜里,人会像一条失去了方向的虫子,在焦急地探索,忘了这本该是静下来的时候,应该蜷在月色中,听山里的虫声唱一首听不腻的歌。就像现在。住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是幸运的,不过人很容易忘记自己所拥有的好,我已经很久没爬山了。今天也只是因为重阳节,仪式性地登高罢了。数月未曾下过雨的山林干涩得很,植物看上去有点无精打采的,并不是特别招人喜爱,但月光会掩饰很多,让人不那么焦虑。此月此山彼时夜,也不知都有些什么人走过?想到可能是好脾气的林语堂,也可能是鲁迅或者是与他不对付的顾颉刚,就会觉得这山路突然变得有趣了一点。就这样,一个人瞎想想,一个人偷着乐,一个人自己都忍不住笑自己矫情。傅抱石画紫竹梅是原产墨西哥的多年生草本植物(鸭跖草科紫露草属),国内大多数地方都有引种,如今甚为常见。但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小县城里它还是稀罕的。我去同学家玩,看到他父母养的几盆紫竹梅摆在门口的台阶边,紫盈盈的,枝叶张牙舞爪,却像一只只毫无威胁小奶猫,问是什么花?说是紫罗兰,就这么误会了好些年。这误会并没有什么不好,紫竹梅比真正的紫罗兰更符合我对这三个字的想象。后者只是花是紫色的,紫竹梅不一样,细圆平整的叶、尖如鸟喙的苞片、挺直有节的茎、细小娇嫩的花,全都是紫色的,而且泛着细微的沙粒状的晶光。那时候我偶然读到罗曼.罗兰,便固执地以为匍匐低矮的紫竹梅上的光就是罗曼.罗兰笔下的那种“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”;还有,“紫罗兰”三个字与罗曼.罗兰再配不过了不是么?天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。怎么样?要不要与我一起,干了这杯月老喝醉酒式的“拉郎配”、一个脑洞失调的跨种族CP?据说月光会诱发敏感的神经产生变异,疯子、天才、还有狼人都可能在月夜里变身。我坐在山脊上,看着月光如水,却被大海吞噬,留下黑洞洞的视界。我企图在城市的车流声里分辨着海浪的节奏,但徒劳无功,我知道我不是天才,更不是狼人,所以……我什么都不是,我只是想起很多,又忘记很多的一个人,一个闲人。秋风起,读书时欢迎点击以上链接购买厦门山鹰 喜欢有赏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yazhicaoa.com/ytcxz/1194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转告大家神奇中草药竹叶莲,见过吗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